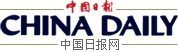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英文《中國日報》6月11日評論版頭條:美國財長來訪,中國外匯儲備的“運用”問題再次成為各方熱論的焦點。
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出動財政,放松金融,大搞財金組合型擴張政策,美元信用下滑,美國國債價值風險上升,各國開始尋找卸載美元,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結構的新路徑。
誠然,針對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適時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結構是合理的。但在此應引起注意的是,外匯儲備資產結構的調整,并不等于外匯儲備的“運用”,甚至濫用,不宜忽略外匯儲備體現著“國家信用”的根本屬性,更不宜混淆“外匯儲備”與“民間儲蓄”的本質不同。因此,如何維護合理的外匯儲備資產結構,就不能簡單套用民間投資的一般邏輯,而必須從國際政治與外交的戰略高度,維護和充實國家的“國際政治威信”和“國家信用”。
首先,外匯儲備是一國對外支付能力的象征。通常,一國對外支付能力主要體現于一國總進口貨款的信用保證能力,其直接表現就是外匯儲備的充實程度。從傳統理論上講,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存量至少應滿足三個月的進口總額,而發展中國家則需要滿足六個月的進口總額。而隨著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發展,國際炒家勢力膨脹,金融交易規模擴大,國家對外支付能力又必須體現包括債權債務的總體清算能力。由此,傳統的外匯儲備存量底線也不斷被修正,以至于各國不得不依據國內外環境、形勢的變化,增加外匯儲備。特別是進入21世紀,石油等國際戰略資源價格波動,呈現總體上浮趨勢,外匯儲備的充實度上升為一國是否有能力維護戰略資源安全的指標。
其次,外匯儲備體現“國家信用”。東亞金融危機后,為避免重蹈金融危機覆轍,東亞各國格外注重外匯儲備的蓄積,意圖性地增加外匯儲備,強化國家對外支付能力、債務清償能力,以及抵御國際炒家狙擊本國貨幣和金融體系的能力。正是這種國家能力的蓄積,為東亞各國貿易、投資穩定擴張,經濟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國家信用”基礎。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能否確保外來投資穩定流入,不僅僅在于“市場利潤”和“勞動紅利”,“國家信用”以及由此衍生的“國家風險”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極其重要的前提條件。其核心直接體現為外匯儲備的充實度和穩定度。
最后,外匯儲備體現一國的“國際政治威信”。2001年中國入世,展開包括歐美日的全球市場,投資涌入,貿易發展,外匯儲備快速增加,2005年首次超過日本,占據全球第一的戰略位置,由此形成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國際政治威信”。縱觀21世紀的新十年,國際社會的大事小情,都無法忽視中國的存在;2008年北京給世界帶來了“無與倫比”的奧運精彩;而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震災,以及全球金融海嘯,都未能撼動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地位,以至于美國不得不放下世界頭號霸主的架子,與中國搞戰略合作,甚至欲結成G2體制等等,其背后無不折射著中國的“國際政治威信”。而中國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的地位,堪稱這種政治威信的財富基礎。
由此,對于改革開放30年,步入世界體系30年的中國而言,蓄積了接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既是空前壯舉,值得驕傲,更需謹言慎行,倍加珍視。維護合理的外匯儲備資產構成,確保外匯儲備資產穩定,則成為確保中國對外支付能力、國家信用和國際政治威信的戰略課題。
因此,中國外匯儲備的資產選擇,就不是簡單的“資產運用”問題,更不應該是“投資”的問題。其原則應是“確保安全”、“確保穩定”和“確保國際政治威信”。由此,任何高風險投資、商品性資產采購,乃至“揮霍性對外轉移”,都不符合中國當前乃至未來一段時期的根本的戰略利益。而從技術層面上看,具體選擇什么資產作為外匯儲備資產,則宜著眼國際政治、外交大局,綜合評定資產的安全性、穩定性以及國際流動性,而不是追求高風險、高利得的“收益性”。(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劉軍紅 編輯 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