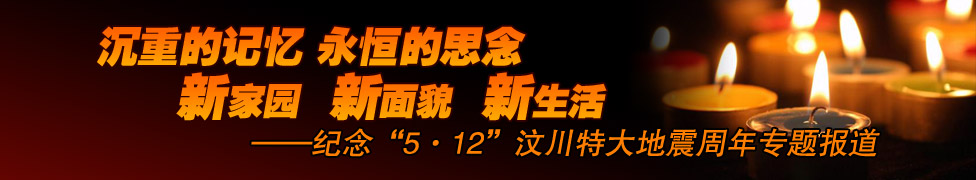主持人:
你看這個馮翔,他參加過心理的咨詢,但是這些咨詢好像還是沒有阻擋他選擇離開的道路。
白巖松:
我個人首先覺得,每當有一個災區的干部或者說是一個同胞,突然因為心理問題或者自殺離開了人世間的時候,大家都會立即想到的是心理輔助,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思維,因為想要幫助他們,在心理上幫助他們,僅有心理醫生是不夠的,它必須有相關的政策,有周圍人的更加敏感,以及整個的氛圍共同構成這樣一個心理的網,僅僅說就靠心理醫生我覺得是太難的事情了,更何況在這次災區重建的時候,我們也要提出這樣的一種反問,很多的項目都細化了,但是在災區重建的過程中我們有心理重建的項目嗎?好像沒有。
另外,我們是建了很多的心理咨詢的醫院,但是都是坐等人們上門來就診,但是又有多少人,本來他的心理就遇到了很大的問題,你認為所有的人都會主動去醫院接診嗎?反而需要走出去,到他們的身邊,我覺得這是從心理咨詢的角度來說,而且一定得是長線的,我覺得現在一種模式很重要,什么樣的模式呢?應該是培養一根又一根的火柴,在災區去培養一根又一根的火柴,讓火柴慢慢地把周圍的人群點亮,什么意思呢?僅僅依靠像志愿者一樣,到了地方,呆一個月走了,不行,一定要在當地中土生土長的去培養很多過個具有心理救援能力或者心理觀察或者咨詢能力的人,慢慢培養他們的能力,最后讓這樣的星星之火去燎原幫助更多的人。
主持人:
但這是一個長期的工作。
白巖松:
但是要做,可是另一方面來說,更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個心理醫生,還需要相關的政策,比如說目前馬上就要迎來5月12日,一周年,我知道這個時候我們很多報道,我們很多人都會看到,這一年災區發生了太大的變化,對嗎?房子都建起來,我們就急于會在報道當中報道,或者說去說周圍的人都形成了這樣的氛圍,災區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我覺得這個時候要慎重,成績放在那兒,不會跑掉的,但是當我們過于強調成績的時候,會讓很多心里面很痛苦的人們產生一種很大的落差,他會去想,我為什么沒有體現到這種幸福,我怎么了,他會更加有一種很難受的感覺。
我也注意到四川的某位領導在講話時說,我們現在災區的絕大多數的人都已經走出了心理陰影,我們已經非常喜悅地投入到建設之中等等,我看到這樣的話時我知道他是好心,其實他也可能也是一種慣性,慣性的一種文字稿子延續下來,但是我特別想提醒我們四川或者是很多地區的領導干部,不要這么講話。
主持人:
你覺得會傷害到那些還是會在心理陰影中的人?
白巖松:
當然,因為你的講話中已經明確地說了,我們大部分的人都已經走出了心理陰影,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建設之中的時候,依然很痛苦在思念自己的孩子,思念自己親人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是少數派,是邊緣的,它會更加放大這種難受,我覺得這個時候要有一種同舟共濟的感覺,有成績以及這樣一些東西我們不著急,留幾年再去說,董玉飛、今天馮翔這樣的事情,都在提醒我們,其實心理的廢墟還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
主持人:
這個時候我們局外人特別想為災區的人做些什么,物質上的東西可能我們都看得到,而且好做,剛才你說,其實心理上的支持更多是一種志愿者的方式,我有空我去,但這個能解決多大問題?
白巖松:
沒錯,所以我們正是要把心理重建納入到我們更大的規劃當中,這樣從國家包括從民間或者更多的力量,包括資金、人員投入其中,另外迅速轉變一種模式,不再是空投式轉身就走,心理救援一定要變成永久式的心理救援,而且要更潤物細無聲,讓它更容易接受,這就要培養當地的人開始成為這方面的能手。
另一方面我也在想這個問題,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接連的兩個都是干部,都是男性,都年輕,而且都是受傷,在地震當中都有這樣的心理受傷的經歷,有的時候男性好像更脆弱,干部也就意味著他面臨的壓力要更多,他不僅面臨生活中的心情中的壓力,也要面臨工作中瑣碎的壓力,而且你要知道,當他是干部的時候,有的時候錯綜復雜的一些東西,我想這么干,可是短時間內不可能這么干,他的那種難受也會加勁,所以我覺得現在災區的干部的確要投入更多的重視,更多的心理扶持,我覺得如果要不是的話,他們要比其他人承擔更多的壓力。
編輯:肖亭 來源:CCTV《新聞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