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教師夫婦為給孩子創(chuàng)造無污染環(huán)境遁入深山
2011-04-18 17:10:52 來源:羊城晚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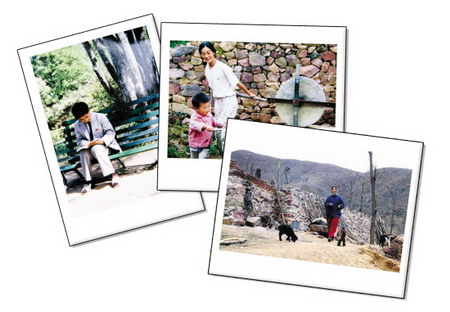 張梅與孩子一起勞動王青松曾是北大的好學(xué)生十幾年間張梅只出山兩次 他從這個世界消失了十幾年,上世紀90年代初拋下一切,攜手同是北大教師的妻子張梅遁入深山,尋找他們心中的“桃花源”。在王青松眼中,外面的世界走著一條和他相反的道路。當(dāng)兩者漸行漸遠,他還能夠和這個世界再次對話嗎? 遁世者 曾是主流意義上的好學(xué)生 3月19日,新華社記者唐師曾接到一個電話:“我是王青松!”曾經(jīng)熟悉的信陽口音讓唐師曾猛然回過神來,這是他消失多年的北大國政系79級同學(xué)。十幾年來,他杳無音信,只偶爾活在老同學(xué)的各種猜測里,出國了,出家了,自殺了…… 在國政系79級的58人中,22歲的他以河南信陽機要干部出身的“老大哥”形象出現(xiàn),一來就被任命為團支書。在上世紀80年代的北大,王青松是個主流意義上的好學(xué)生———北大國政系79級學(xué)士、北大法律系83級碩士畢業(yè)留校任教。同學(xué)們也不理解,他怎么會把這一切都拋棄了。 人生轉(zhuǎn)彎 內(nèi)心里總會走到這一步的 一次偶然的機會,讓王青松的人生轉(zhuǎn)了彎。他從小練過武,到北大后又愛讀老莊,1985年“養(yǎng)生熱”時,開始在北大教授養(yǎng)生。 養(yǎng)生為王青松帶來了聲名,還有財富。他成了北大一協(xié)會的明星,后來法律系看他影響大了,讓他為系里創(chuàng)收,在外開設(shè)一周養(yǎng)生班,每人收費10元。后來成為他妻子的張梅也是學(xué)員之一,剛從北京外國語學(xué)院畢業(yè),比他小12歲。 1990年后,他從頂峰跌落。“當(dāng)時,我報考哲學(xué)系湯一介先生的博士生,單科和總分都考了第一名,學(xué)校竟然不予錄取。第二年轉(zhuǎn)考法律系,依然。”另一方面,他覺得對養(yǎng)生已經(jīng)研究透徹了,已經(jīng)滿足不了他的內(nèi)心需求。 王青松覺得隱居的根本原因是自己對內(nèi)心的關(guān)注,而現(xiàn)在的社會大方向則是向外看。他愿意知行合一,把向內(nèi)同時作為一種人生實踐,回到山里看看古書,養(yǎng)個兒子。而驅(qū)使他們一步步遠離人群的一個引子,只是“為了吸一口新鮮空氣”。 王青松1994年搬到北京與河北交界附近的山區(qū),那里有座岳父的老房子,租地10畝。去北大上一次課要坐5個多小時公交車,耕地也無人照管,于是妻子張梅在1998年毅然辭職,而他則在2000年后脫離北大,承包荒山2500畝,從此與世隔絕。 回歸之路 兒子的路由他自己選擇 張梅說,當(dāng)年促使他們徹底離開人群是因為想給孩子創(chuàng)造一個無污染的成長環(huán)境。十幾年間張梅只出山兩次,一次是換二代身份證,一次是存折掛失。 如今,兒子7歲了,張梅拿“人大版”的小學(xué)一年級課本教他,每天三節(jié)課,語文、數(shù)學(xué),英語。兒子半耕半讀,上午學(xué)習(xí),下午放羊,智力之外,體能也比城里孩子強。 王小宇生下來基本沒出過山,只有收音機接收信息。看到兒子見到外人的興奮勁,王青松說,他作為父親覺得很內(nèi)疚。孩子的教育怎么辦?是不是該回歸社會教育?王青松覺得,這也是兒子的權(quán)利,以后的路,要由他自己選擇。想為兒子開設(shè)一個與社會交往的綠色通道,成為王青松準備回歸社會的最重要原因。 來源:羊城晚報 編輯:孫遲
|
|
|
|
|
|
|
| 商訊
|
專題
|
各地新聞
|
|
|
點擊排行
|
視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