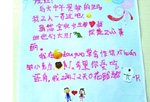求是:中國社會道德變革進步有目共睹
認清道德主流 堅定道德信心
——再論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階段道德狀況
作者:秋 石
一段時間以來,道德議題的熱度持續走高,對道德問題的關注,成為社會輿論特別是各類媒體常說常新的話題。無論是贊美道德模范的感言,還是抨擊敗德現象的批評,似乎都在印證這樣的評論:2011年我國社會出現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動與疼痛并存,譴責與反思交織,憂慮與希望同在”的圖景。論辯各方對道德問題超乎尋常的關注和唇槍舌劍,折射了中國社會深厚的道德底蘊和中國人濃重的道德責任心結。從一定意義上說,一個社會真正危險的道德狀況,不是人們對敗德現象的義憤,而是對道德滑坡的冷漠。無論是感動還是疼痛、譴責還是反思、憂慮還是希望,都傳遞著社會公眾的善良意識和德性本質,反映出干部群眾的道德自省和道德愿景,也充分證明我國社會的主流道德觀念、主流道德行為和主流道德輿論的積極、進步、向善。信心比黃金更珍貴,道德的信心,正源自于主流社會更加強勁的道德呼喚和吶喊。
一、看待道德狀況的歷史坐標
評判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狀況,需要選擇并確定具體的歷史坐標。道德從來不是凝固不變的,道德在歷史中生長變化,道德只有在歷史的比較中方能衡量進步還是退步。我們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各項事業包括道德建設事業取得了歷史性進步,一個基本的依據,正是對過去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進行的歷史比較。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一切親身經歷了這三十年偉大變革并貢獻了自己力量的中華兒女,一切關心祖國命運的華夏子孫,都有理由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成就感到自豪。”在改革開放全方位的歷史性成就中,毫無疑問,道德的歷史性成就占有一席之地。看不到當前存在的一些道德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就會喪失警惕,是危險的;看不到30多年來中國社會道德建設的成就和主流,就會喪失信心,同樣是錯誤的。
毛澤東同志當年在評價歷史上的革命時代時曾說,“奴隸制的產生在當時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因為奴隸主不殺俘虜,而是拿俘虜做奴隸,雖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傷他一只手,但總還是要讓他做工,奴隸制可以積累財富。這個思想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說:“在道德方面也和人類知識的所有其他部門一樣,總的說是有過進步的”,而且要看到“每一次革命的勝利帶來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躍進。”經典作家是拿昨天和今天進行歷史比較,堅持的是歷史進步的標準。
現在國際國內都有一種靜態地評價中國道德狀況的輿論,拿一種固定的標準或既有的模式來衡量中國的道德狀況。比如,在人權問題上,認為中國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比還有這樣那樣的差距;比如,在社會公德問題上,認為中國人不遵守公共秩序,特別是不遵守交通法規等;比如,在家庭關系問題上,認為中國社會還存在很多嚴重的“家庭暴力”現象;比如,在慈善問題上,認為中國社會的慈善捐贈數量還十分蒼白,等等。這些看法的結論就是,既然存在這么多道德問題,怎能輕言中國道德狀況的主流是積極、進步、向善的呢?
實際上,這種靜態地評價中國道德狀況的輿論,其選擇的歷史坐標,要么是西方發達國家經過很長的歷史發展過程才達到的標準,要么是中國正在繼續努力的未來目標。這樣的視角,是從國外發達社會看中國,或者是從中國的明天看中國的今天。
但是,如果把歷史坐標定在改革開放前,定在新中國建立前,選取從中國的昨天看中國的今天的視角,結論就完全不同。在人權問題上,中國自近代以來經歷了艱苦的斗爭和歷史的曲折,從爭取人權,到回避人權,再到人權“入憲”,這樣的歷史進步,是誰也無法否定的。在社會公共秩序問題上,中國普通百姓擁有私家車的時間還不及西方國家的零頭長,今日中國人遵守交通法規的情況,遠比西方國家汽車普及早期的情況要好得多。在家庭關系問題上,諸如“打老婆”、“打孩子”這樣一些“家暴”現象,過去至多被認為屬于封建陋俗,只會受到家人鄰里的指責和單位組織的批評,甚至還會有人認為這只是“清官”難斷的“家務事”,丈夫打老婆“天經地義”,“棍棒底下出孝子”。但在今天的中國,法律對“家暴”有了明確態度,“家暴”不再只是“家務事”,而是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在慈善問題上,慈善事業在當年被不分青紅皂白地劃在資產階級的“偽善”范疇之內,哪里會有今天這樣以中華慈善總會、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等十大慈善機構為代表的各級各類的慈善組織及“光彩事業”。據民政部統計,截至2010年底,全國已建立3.1萬個經常性社會捐助工作站(點)和慈善超市,初步形成了多種類型、分工協作的社會捐贈網絡;社會捐贈數額2006年首次突破100億元,以后逐年上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更是引發捐贈熱潮,社會捐贈總額突破1000億元。
上述實例恰恰證明了自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德所取得的歷史性進步。在這些問題上,中國社會的道德觀念、道德規范、道德實踐和道德評價標準的變革進步,是客觀真實和有目共睹的。
對這樣一些片段性的實例進行討論的一個方法論意義,是可以啟發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對道德狀況本質的判斷,首先在于選取恰當的歷史坐標,這樣才能正確看待道德的問題和成績、支流和主流的性質與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