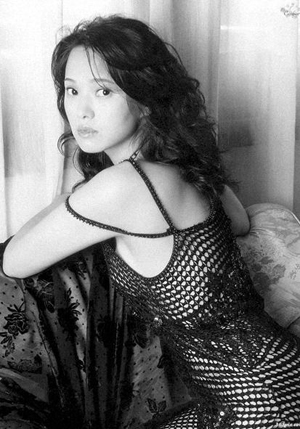 據野史《趙飛燕外傳》所記,飛燕本是漢宮中一名歌妓,由于身輕善舞,深得漢成帝喜愛,召入宮中被封為皇后。飛燕后來又將妹妹趙合德引入宮中,推薦給成帝,封為婕妤。不久,成帝專寵合德,而冷落了飛燕。二人雖都是體香貌美的絕世佳人,但體香的來源卻不一樣,以至竟因此而導致了一場爭寵的宮廷悲喜劇。
據野史《趙飛燕外傳》所記,飛燕本是漢宮中一名歌妓,由于身輕善舞,深得漢成帝喜愛,召入宮中被封為皇后。飛燕后來又將妹妹趙合德引入宮中,推薦給成帝,封為婕妤。不久,成帝專寵合德,而冷落了飛燕。二人雖都是體香貌美的絕世佳人,但體香的來源卻不一樣,以至竟因此而導致了一場爭寵的宮廷悲喜劇。
據說成帝曾私下里對人講:“后(飛燕)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于是飛燕為了和體有“天香”的妹妹爭寵,奪回自己失去的地位,便想盡辦法來增添體香:“浴五蘊氣香湯,踞通香沉水座,燎降神百蘊香,傅華百英粉”。這個故事表明女性的體香有天然與人工之別,但遺憾的是這種“天香”并非人皆有之。
香妃的故事也可以體現對中國女性自然“體香”的推崇,據《清史稿·后妃傳》中的容妃,維吾爾族人,于乾隆二十五年入宮,初封貴人,后升為嬪,又晉封為妃。清代野史中寫道:“回部王妃某氏者,國色也;生而體有異香,不假薰沐,國人號之曰‘香妃’。”還說當時乾隆聽說香妃美艷過人,中原無人可比,便命大將軍兆惠舉兵西進,一定要得到香妃。兆惠不負君命,將香妃捉到并送到了京城。
香妃入宮后,深得乾隆皇帝的喜愛。但是,香妃并不喜歡宮廷里籠中鳥般的日子,終日郁郁寡歡,又因為“香”而被人嫉妒,所以很早就香消玉隕了。
一般的女性想要擁有誘人的體香,就需要用薰染的方法來增添身體的香氣,或者除去身上的難聞氣味,以彌補先天不足。李漁承認了“國色天香”的可遇而不可求,認為薰染是正當的,“有國色而有天香,與無國色而有天香,皆是千中遇一;其余則薰染之力,不可少也。”
女性對于體香的重視,在《紅樓夢》中可以找到許多例子,在第六十二回中史湘云醉眠的情節中:
都走來看時,果見史湘云臥于山石僻處一個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邊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鬧嚷嚷的圍著他,又用鱎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著。眾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挽扶。
史湘云喝醉了酒,為圖涼快就在石凳子上睡著了,饒是如此,她還記得要“用鱎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著”,可見薰香已經成為那個時代女性的集體無意識了,自覺或不自覺的希望通過薰香來錦上添花,在這一段中史湘云酣睡在花香中,就連蜂蝶也被花香吸引,怪不得惹人憐愛。
又如在第十九回中:
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卻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銷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籠著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誰帶什么香呢。“寶玉笑道:既然如此,這香是那里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頭的香氣,衣服上薰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畢。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
黛玉的體香令寶玉“醉魂銷骨”,但是她卻千方百計掩飾這種體香的來源,偏偏不讓寶玉看自己的袖子,這體現了黛玉的一點小小心計,神秘的物件永遠具有別樣的強烈吸引力,如果謎底被揭穿反而有些索然無味,因此女性的閨房中香囊等薰香物件是密不示人的,除非她將自己的未來完全托付給某個男子,才會“香囊暗解,羅帶輕分”。
古代女子的增香之法,大致可以分為薰、沐二類。所謂“薰”,本義為薰草,又名佩蘭、零陵香。關于薰草,《山海經》中記載說:“浮山有草焉,名曰薰。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蘼蕪,佩之可以已癘。”薰是一種天然香草,有著增添香氣和祛除臭味的用途,所以獲得了中國人格外的青睞,古人或將它佩戴在身上,或榨出草汁涂在身上,或焚燒來取其香氣。由于薰草的這種特殊的增香作用,后來也用“薰”來泛指其他的一些香草及其香氣。